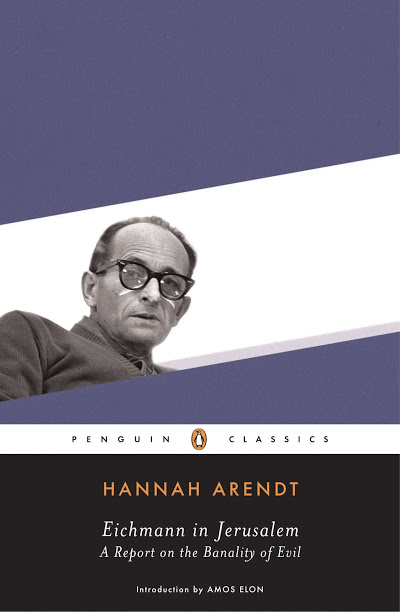
banality of evil
孔誥烽 2013年8月19日
上兩個星期天,旺角和天水圍街頭分別發生了兩宗親建制力量以暴力招呼反對派的衝突。衝突之後,有不少論者慨嘆「香港社會撕裂」、「走向兩極化」。有雜誌甚至以「香港政治以激鬥激」為封面。這種論調的言下之意,是「社會分化」很不好,大家應該各讓一步,尋找共識。更有文人呼籲大家記住親建制的施暴者,也是我們的鄰舍,所以我們要同情地理解他們。
和稀泥有如助紂為虐
這種各打五十大板、你有不對我又有不對的和稀泥觀點,在無可無不可、只求乾淨人人愛的好學生當道的香港,一向流行。但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我們更應該用理性去明辨對錯、取捨立場。該分是非黑白時不去分是非黑白,很多時候便等於助紂為虐。
在藍營、綠營和北京都有不少影響力的台灣政治評論大老南方朔先生,最近便在〈要講道理不和稀泥〉一文中,狠批這種不問是非曲直,偽裝超然的造作姿態:
「『和稀泥』是慣於妥協忍讓的討論方式,但往往模糊焦點、混淆是非。民國早期的學問家梁漱溟先生,曾寫過《中國文化要義》一書。他在書中指出,中國文化的致命缺陷,乃是早熟早衰,形成一種不講道理,只是忍讓、和稀泥的習性,大家都因循苟且地度日。這也造成了古代中國只有王朝反覆,而無進步的結果。他所謂的『不講道理,只是忍讓、和稀泥』,讓我想到台灣最近的兩岸爭議……
「(例如)台灣的全民健保,是國民的基本權利。陸生是客,不在『全民』定義的範圍內,因此陸生的健保應與外購買商業保險。但政府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卻硬要將陸生納入全民健保,並說反對的人是不人道、太小氣。其實,這個問題根本就跟人道與小氣無關,只和國民的權利義務有關。把問題扯到人道和小氣上,真的是『和稀泥』……
梁漱溟先生指出,中國人的麻煩是,從不會用稍微抽象的理念,去議論事情的是非對錯,或權利義務、公平正義等問題。而只會淡淡地用忍讓、和諧等模模糊糊的道德概念談問題。這因而造成中國人思想的渾沌不清。梁漱溟先生當年曾表示,這種和稀泥的談問題方式,是中國不可能產生民主法治的原因。」 (《天下雜誌》2012年10月31日)
是少數人要建立暴政 不是社會分化撕裂
在旺角發生的衝突,起因於休班路過的林老師,看不過眼警方偏幫在街上騷擾法輪功的親建制組織,在與警員爭執時爆了一句很多高級中產在觀賞大卡士西片時也常常聽到的英文粗口。之後親建制團體和警察團體排山倒海地批鬥林老師,其任教學校門外更出現文革式標語和花圈。親建制團體和休班警員在旺角閙市舉行集會聲討林老師。當中有支持林老師的市民和在當場採訪的記者被推撞攻擊。
整個事件,明顯是建制派利用一件小事借題發揮,打開親建制團體以文革手法對付異己的缺口。先例一開,恐怕以後有老師用公餘時間宣傳、參與佔中運動,也要害怕成為那些團體威嚇騷擾的對象,飯碗不保。事後特首一再敦促教育局聯絡林老師的學校調查事件,之後向他交報告。這件事背後的政治動機,還不夠清楚?
在這事上,香港社會有撕裂嗎?美國支持民主黨共和黨的選民接近一半一半,台灣藍綠支持者人數相當,當兩派矛盾激化,便叫撕裂。現在香港的民意,不論是通過媒體輿論和各式各樣的意見調查,或當日旺角反對和支持林老師的人數對比呈現出來,都是一面倒的。警員參加政治集會和有人以黑社會手法騷擾學校,更是嚴重踐踏香港一直以來的公民共識。
既然民意一面倒,又何來撕裂?現在明明就是有一個反動保守的小集團,以極端手法逆香港的核心價值而行,試圖建立粗暴的少數人專政。隨後的星期天特首到天水圍落區時,亦有疑似黑底人物襲擊反梁示威者,事件的性質再清楚不過。
如果連在這種事情上,我們也能和稀泥,那麼下次我們看到好色梁伯強暴少女虹虹,虹虹勇武反抗罵髒話和抓了梁伯兩下,我們恐怕也要同情地理解梁伯為何要強暴,勸告梁伯與虹虹不要兩極分化撕裂雙輸,呼籲他們努力化解矛盾、尋求雙贏共識了。
兩次衝突後,也有人因為暴力自1967年後首次再度進入本地政治而感到哀痛悲觀。但正如香港一名曾因為偷步買車(相對今天梁粉門的胃口,何其雞碎!)而下台的高官說過,一個最壞的時代,往往也是最好的時代。香港搞成這樣,當然可能是漫長黑暗的前奏,但也可能是否極泰來的黎明。
只要大家說不 暴力難以得逞
曾提出「平庸之惡」(banality of evil)論,指極權體制往往建基於無數平常人共犯的政治思想家Hannah Arendt,在臨終前不久的1969年於New York Review of Books發表一篇名為〈反思暴力〉的長文,指出無論對於當權者還是革命者而言,暴力都無法創造權力,反而會摧毁權力。
Arendt認為,權力的基礎,在於眾人的共同意念與認可。一個具有權力的政府,並不需要暴力;一個政權只會在喪失合法權力之時,才需要使用暴力維持統治。而暴力的使用,將會進一步消耗施暴者的權力。歷史上有不少政權的確成功利用暴力來延續壽命,但這並不是因為暴力增加了政權的權力,而是因為被暴力嚇倒的民眾,不敢施展他們的潛在權力。只要人民無畏暴力大規模地聚集起來,拒絕與政權合作,新的植根於人民的權力便會在街頭誕生;舊政權無論有多暴力,也必然倒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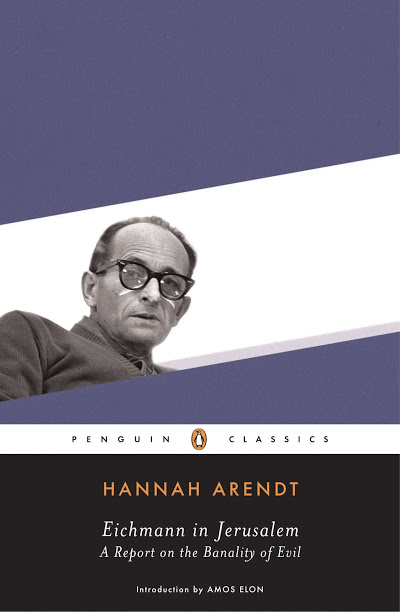
banality of evil
Arendt這個觀點,與其「平庸之惡」論一脈相承:如果惡棍專制者竟然能夠通過暴力保持權位,在面對暴力時沒有大聲說不、靜靜地與施暴者合作的「沉默大多數」,要負很大責任。若這個大多數不沉默,暴力根本無法得逞。
自1970年代的連串社會行政改革起,獲得了民心與權力的香港政府,已經愈來愈少使用暴力。在特區現政府被一個比一個嚴重的醜聞衝擊後,暴力的潘朵拉盒子被打開了。這證明這個政權已經喪失權力、眾叛親離,無法再叫港人齊心在它的領導之下。我們到底是要向這個走投沒路的虛怯政府大聲說不,送它最後一程?抑或是沉默地看着暴政生根固化?這是每個香港人都不能逃避的抉擇。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副教授